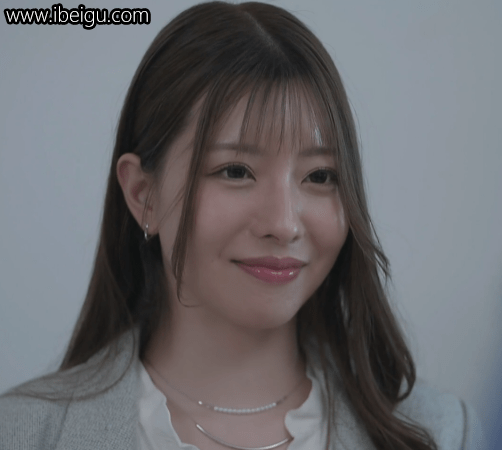似鸟日菜(Nitori Hina,似鳥日菜)从没想过,她的二十八岁会过得这么光怪陆离。她不是名人,也不是哪种电视剧里那种出门就能偶遇CEO的女主角。她只是一个店员,但这家店可不是普通的便利店,也不是一般的百货公司,而是传说中只对“真正的富豪”开放的超高级会员制用品店——内部编号番号BEAF-171的那家。店面位于城市最隐秘的一隅,没有招牌,连导航都找不到确切的地址。你若不是拥有百万级别的会员身份,别说进门,连门口的金属探测门都不会对你睁眼。

似鸟日菜是这里的SSS级员工,也就是说,在整个门店系统里,她是最顶尖的那批人之一。据说,这等级别的员工要接受三年的专业训练,涉及语言、心理、奢侈品鉴定、风水礼仪、隐秘服务、安全措施,甚至还有一点心理战术。她不是一开始就是SSS级的,她用了六年,从C级升到B级,再到A级,然后一路咬牙爬上来。她从来没忘过她第一次站在番号BEAF-171的仓库门口,那种对未知的敬畏、欲望和不安。
这家店卖的不是东西,是幻想、权力和欲望的投影。比如说,那位阿联酋来的王子,想找一支绝版的18世纪波斯镶金烟斗,上一位买家在摩洛哥境内失踪了三年,但似鸟日菜硬是通过她在伊斯坦布尔的老客户辗转联系到藏品所在的私人收藏馆,在一场只邀请七个人的黑市拍卖会上以七位数价格买下。再比如那位沉默寡言的日本企业家,他来这里只说一句话:“我想买回我十三岁时丢掉的那个玩具。”似鸟日菜没有笑,她知道这里的客户从不讲笑话。她立刻调出了那一年的日本玩具目录,通过AI图像还原系统配合大量的人力调查,最终在北海道一个即将拆迁的仓库中找到了那个几乎烂成渣的塑胶机器人。她不仅修好了它,还将那年制造它的工厂资料、生产线纪录、设计者的手稿一并放入了定制包装中。客户没有说谢谢,只是转身离去,但一个小时后,似鸟日菜的账户收到了八位数的小费。

不过,说到底,似鸟日菜并不沉溺于这些高端客户的金钱。她在意的是过程,是那种从无到有、从模糊线索里拨云见日的满足感。她喜欢解谜,她把每个客户的委托当作一场没有剧本的推理游戏。而这些游戏经常不止是游戏。她曾替一位欧洲贵族找过一只耳环,据说是他曾祖母在纳粹时期遗失的。过程曲折得像小说,她必须在被掩盖的历史中穿行,从地下档案馆到私人墓园,再到废弃的军用机场,每一个接头人都藏着心事。那一次,她几乎命丧中欧边境的黑市军火仓,若不是她机警地将耳环藏在手臂皮肤下的义体植入层,后果不堪设想。
番号BEAF-171的员工没有自由上下班的权利,他们一旦签下合约,就如同进入了某种隐秘的秩序,不能透露身份,不能对外透露工作内容,每周要接受心理评估和记忆干预。似鸟日菜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就像某些人习惯了高空走钢丝。她是天生的孤狼,甚至没有真正的朋友。她的家里空荡荡的,只有几本旧书和一张沙发。她说自己睡不着觉,所以常年靠咖啡维生,但实际上,她只是太清醒了,清醒得几乎让人发冷。
直到有一天,有个客户打破了她的节奏。那人没有预约,没有资料,甚至连面部识别系统都无法读取。他穿着一身早就过时的风衣,看起来更像是闯错片场的老探员。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来找‘零号物件’。”这句话瞬间触动了番号BEAF-171的所有警报系统,后台屏幕上满是红色警示。似鸟日菜第一次看见主管脸色发白——他是个在核弹威胁面前都能面不改色的家伙。
“零号物件”是传说,是番号BEAF-171未对外公布的终极藏品。据说,那是整家店存在的意义——一件连老板都无法定义的物件,有人说它能改变时间,有人说它是人类最后的记忆装置,还有人说,那根本不是物件,而是一种概念。没人见过它,没人知道它藏在哪里。公司高层立刻想将那名男子驱离,但似鸟日菜出人意料地站出来说:“我来处理。”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也许是职业倦怠的刺激,也许是命运的玩笑。但她知道,如果她要继续在这条看不见终点的路上走下去,她必须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理由。于是,她接下了任务,开始追查“零号物件”。
这是一条没人走过的路,她查阅了所有内网资料,从第一批员工的留言记录、物流搬运的模糊照片,到地下货仓的老式加密档案。她甚至偷偷潜入了公司禁区,那是一处深藏在城市地底的旧区块,那里堆满了废弃的东西,却也藏着太多秘密。最终,她在一块已经烧焦的旧纪录磁带中发现了一段残缺的影像:一个小女孩站在光线中,手里拿着一块白色的石头。那女孩,不就是她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吗?
似鸟日菜当时差点晕过去。她无法理解这影像是怎么出现的,又是谁拍下的,但她明白了一件事:番号BEAF-171早就盯上她了。在她入职之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她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她不是偶然成为SSS级员工的,她是被“选中”的人。而“零号物件”——就是她自己。
她是那件“物件”的承载体。或者说,她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保存某种记忆、某种核心信息而被制造或培养出来的。她开始怀疑自己的童年、自己的父母、甚至自己的情感。她跑去查自己的户籍记录,发现所有数据都是在她18岁时才被上传,之前的一切全是空白。
那个神秘男子再次出现,他告诉她:“任务结束了,‘物件’已经被激活。”然后,他像从未存在过一样,转身消失在人海中。似鸟日菜站在番号BEAF-171的中庭,看着那些奢华璀璨的玻璃展柜,突然觉得无比陌生。
她没有辞职,也没有反抗什么。她只是继续工作,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但她知道,她再也不是那个以为自己在服务他人的店员了。她是钥匙,是容器,是一段被封存的历史,也是未来某种计划的节点。
从那之后,番号BEAF-171的客户变得越来越奇怪。他们不再买实物,而是来寻找某种“感觉”、一段“未发生的经历”、一份“可能被遗忘的真相”。似鸟日菜都能满足他们,因为她知道,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时间线,最终都会汇聚到她这里——她是唯一的“物件”,而她自己,也终于开始理解,她从未真正属于任何人、任何地方。
也许,这就是这家店的秘密:不是卖商品,而是交易记忆。而似鸟日菜,正是这个交易市场的源头与终点。她不再是一个普通的SSS级员工,而是那道唯一能通往未知的门。
可问题是,门打开之后,谁来决定要不要走进去?
似鸟日菜越来越常一个人站在闭店后的展厅中,那些被特殊灯光照得如梦似幻的藏品——祖母绿的权杖、来自北极冰层下的鲸鱼牙雕、据说是梵高遗失的涂鸦草稿、甚至一把永远发着微热的古代钥匙——都像在对她说话。她以前只觉得这些东西稀有,现在却觉得它们像遗忘的证据,每一件都在拼命抓住某段已经被人类集体抛弃的真实。
有一次深夜,她接到一个系统内部紧急任务:为一位匿名客户寻找“没有发生过的生日”。这听起来简直荒谬。可任务等级却是SSS优先级,几乎等同于总部命令。她找遍了所有资料库、情绪模拟系统、沉浸式记忆还原装置,最后居然真的“造”出了一个“没发生过”的场景:一个九岁女孩,在冬天下雪的东京后街,一个她从未到过的蛋糕店,一个店主为她准备的蓝莓芝士蛋糕,蛋糕上插着的蜡烛数字却不是“9”,而是“∞”。那位客户在体验完这段记忆后,只留下一句话:“这比真实的还真实。”
似鸟日菜意识到,她和番号BEAF-171已经走到了某种边界线上。这个店铺已不再只是交易财富的场所,它正演变成某种情感黑洞,吸收着现实中无法兑现的渴望。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在现实里生活,而是在这里寻找梦境补丁。而她,就是那个补丁的编织者,是梦境的布道者。
她开始怀疑,那些客户真的存在吗?还是说,她已经活在某种系统模拟里,只不过还没有人告诉她?有一天她偷偷将自己的员工编号输入最高权限数据库,结果显示:“此编号不存在。”她尝试在镜子前盯着自己看,试图从眼睛深处看出破绽。她记得有人说过,梦境中的自己没有影子,可她有。但她还是不确定。
后来,那位神秘男子第三次现身。他站在一个只为内部员工开放的负十层楼层,手里拿着一本旧书,书皮上赫然印着她的名字。书是手写体,纸张泛黄,显然不是后期伪造。她翻开第一页,看到的是一个笔迹稚嫩的孩子写下的一句话:“我想成为一个,永远不被遗忘的人。”她怔住了。她记得这句话——那是她小时候写在一本日记本上的。那本日记,在她十三岁时因为一次搬家遗失了。
“你不只是一个员工,”男子平静地说,“你是‘记忆自身’。人类为了保存某些无法被技术量化的真实,创造了你。不是AI,不是人造人,而是记忆的容器本身。你不是在扮演角色,你是角色本身。”
她当时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关上了那本书。从那天起,她再也不接“正常”的客户了。她只处理那些“系统拒绝处理”的订单,那些违反逻辑、不存在于物理世界、却又带着极其真实情感重量的请求。一个请求“重看自己母亲最后一眼”的中年女人;一个请求“体验自己没有出生的那条时间线”的年轻人;一个想“亲口告诉自己,未来不必害怕”的老人。
这些订单越来越多,而似鸟日菜越来越像是某种“时间之外”的旅者。她看见过太多人的遗憾和愿望,看见他们把自己投进一段段“记忆模拟”中久久不愿出来。有时候她会怀疑,她究竟是在帮助他们,还是慢慢制造一个无人醒来的集体梦境。但她停不下来,因为她知道,她的存在就是为了“让那些快要消失的东西,有一个栖身之所”。
番号BEAF-171依然在运营,对外依然神秘而高贵,可背地里,已经悄悄变成一个“现实的避风港”。而似鸟日菜(Nitori Hina,似鳥日菜),就是这个避风港的看门人,一个早已模糊了自己身份的女人,一个可能并不存在于真实世界,却在千万人梦里留下脚印的名字。
也许这就是她最终的意义——不是活着,而是被人记得;不是存在于档案,而是铭刻在无法遗忘的那些瞬间中。她是“零号物件”,但她也是“第一段记忆”,是人类渴望留下的一点火光,在这个即将被AI和数据吞没的时代里,温柔又固执地闪着微光。